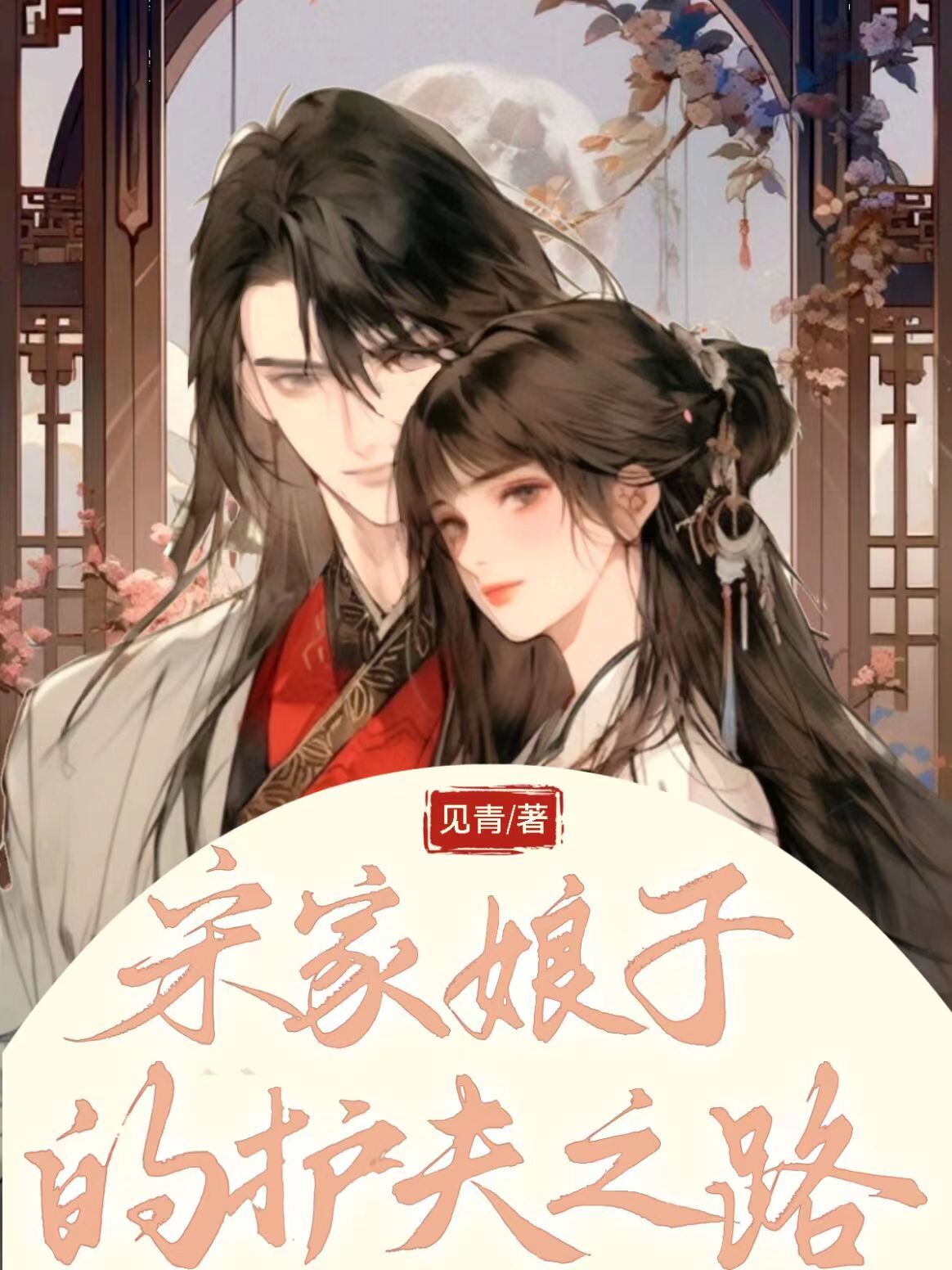第4章交换细帖
对于家中的财产,钟秀花掌握得一清二楚。
“娘,二弟先前打仗带回来的东西和银钱我都给收着呢,全锁在后面那小屋里,每日都要去清点清点。里面有白银五十两,还有好些金项链啊金镯子什么的,奥还有好几箱书呢。那屋子里的东西全拿出来做聘礼,我们大房再添个十两银子,应该能够吧?”
“对对,和石蛋当年娶媳妇一样,我和你爹也出十两银子。”
“娘,嫂嫂!”吴铮有些感动,“家里什么光景我也知道。你们还有元宝和丫丫要养呢,这些钱都是你们的积蓄,给我娶亲了两个孩子怎么办?你们为我好好操持婚事便行,银钱的事儿我自己解决。我这些年还存了二十两的私房钱,都拿去买聘礼!”
“二弟,这怎么行?当年我与你大哥成亲,你还补贴我们大房五两银子呢。”
“哎呀嫂嫂,我那是花钱买平安呢。可得把嫂嫂贿赂住了,我才能有好饭吃呢!”吴铮故意说着玩笑话,惹得众人笑作一团,片刻他又正色,“嫂嫂这事你别再坚持了。我自己想法子去。”
花开两朵,各表一枝。
吴家正讨论二人婚事,宋家也着人去打听了吴家具体情况。
乔氏端坐在上首,听着底下丫鬟的回话,脸色看不出什么,只目光越来越沉。
“回二太太,婢子差人都打听清楚了。”
“吴家原先是西宁州的小门小户,吴小将军得了太子赏识进京,一家人便也都跟了来。”
“吴家二老俱健在,膝下有二子一女,小将军在家中行二。吴家由长房媳妇钟氏掌家,吴大郎君在漕帮码头帮人运货。听闻吴大郎君性情温和敦厚,吴大娘子是一个性情直爽还有些泼辣的人物。二人还育有一五岁哥儿,小名唤作元宝。”
“婢子向四邻打听,街坊邻居都说吴家老太太是一个宽和的婆母,与吴大娘子极为亲近。吴老太爷为人勤恳,在京中寻了一处木匠活计。老太爷极爱逗蛐蛐儿,婢子特意去打听了一番,那赌坊倒是不曾去过。吴小将军还有一个才七岁的妹妹唤作丫丫,听闻是有些呆傻的,但是家中长辈都很是疼爱。”
“吴家府上在外城永安巷胡同口,是一处一进的宅院,从牙行租赁而来。婢子去牙行打听,那牙人说吴家是长租,一月一收,倒是不曾拖欠过银钱。”
“其余吴家在西宁州的事儿,婢子已差人去打听了,约莫再过几日便该有消息传回。”
丫鬟禀告完就低眉垂目站在一边,屋内一时陷入沉寂。
“叮——”
“噔——”
忽起两声清响,是乔氏冷着脸将茶盖扔在茶盏上,随手把茶盏放在了金丝楠木海棠几上。
“欺人太甚!”
乔氏冷肃着一张脸,低声咒骂。
“一家子田舍奴,蜗居在指甲盖儿那么点地方,还敢肖想我暄儿!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!”
“若是公爹在世,先皇在世,我暄儿如何生那大病?生了病又有谁敢怠慢?我爹爹配享太庙,哥哥三元及第,若非罢官不出,宋家这一个两个吃人的东西如何敢欺负我暄儿!”
“可怜她生下来就巴掌那么点大,我小心翼翼养着护着,风大了怕刮着,雨大了怕淋着,日头大了怕晒着,怎么……怎么就摊上那么一家子田舍奴!她在宋家尚且遭人闲话,嫁给那武夫还有什么指头!”
说着说着,乔氏眼中忽然氲出泪来,没忍住抱住徐嬷嬷的腰,低声痛哭起来。
乔氏知道联姻之事大抵与吴家是没有关系的,不过迁怒罢了。
明暄敛眉站在屋外,悄声吩咐仆妇去准备凉水。
门口打帘的小丫鬟瑟缩着身子,规规矩矩立在明暄身后,不敢发出半点声响。
就这样听了好一会儿,等到屋内渐渐安静下去,明暄才侧过身子,示意小丫鬟打帘,领着身后端着凉水的仆妇走了进去。
小娘子亲自将一块素罗帕浸入凉水,而后轻轻拧干,走到乔氏身边,细细为她敷面。
“娘亲平日里不许我哭,说哭大伤身,怎的娘亲自个儿还背着我偷偷流眼泪呢。”明暄一边轻拭泪痕,一边与她逗趣,“看来娘之前与我说的都是假的,我今日回去就好好哭一场,把这些年的金豆子都去哭出来。”
“你敢!”乔氏轻声嗔了明暄一句,脸上倒是轻松不少。
“是是,我怎么敢呢。”
明暄哄着,面上多了几分素日难见的温柔。
“其实娘亲不必如此伤心。方才朝雨姐姐说的我都听见了,那吴家也并非全然不好。吴小将军在京中做官,可是吴大郎君和吴老太爷并不自视甚高全然扒着小将军,也努力做些活计养活家里,可见父兄俱是明理勤恳之人。再说小将军的妹妹,虽说有些痴傻,但是家中长辈都疼爱,心思定然纯善宽厚。我嫁过去,倒也不难相处。加之规距松散,日子岂非快活?”
“吴家一家七口人,都窝在那一进的小院子里。人家一府上下也就比你那栖光院大不了多少,何等憋屈!”
宋家在这都城,是数一数二的清贵人家。
已故老太爷官拜太师,曾是今上的启蒙老师。府内分为两房。大房掌家,宋大老爷现任左仆射,为朝中的正一品大员,膝下共三子二女。其中,大女儿明臻自出生便由官家钦定为太子妃,连“臻”这一字,也是圣人予的。三个哥儿一嫡两庶,嫡子明旸家中行三,为官家钦点探花郎,如今是湖州通判;剩下两个也都取得了举人的功名。
再说二房,宋二老爷任正四品太常卿,位列九卿之首,掌宗庙祭祀之礼。二房共一子二女,嫡子明旭行二,如今在太学治学,剩下的明暄与明晗皆是庶女。明晗行七,由孙小娘自己教养;明暄生母乃是乔氏身边的大丫鬟,难产而亡,自出生起便记在乔氏名下,由乔氏悉心抚养长大。
宋府是两组四进的院子并列在一起的大宅院,老夫人住上房,长房居东府,二房居西府。虽说大房门庭比二房显赫,但因二房主子少,分得的庭院倒还大些。
而且乔氏的母亲乃是江南有名的茶商之女,当年陪嫁多少良田商铺,光是雪花银便近万两。
于银钱上,大房比之不及。
明旭因为是二房唯一的嫡子而得二老爷关注,明暄是自小由乔氏抚养旁人半分不沾的,因此关系十分亲近,恍如亲生母女。
尤其明暄不再去上学后,明旭常年在外读书,明暄一直守在乔氏膝下,乔氏便更加依赖明暄。明暄因为是早产儿,自幼病弱。栖光院是西府除了南春院以外位置最好最大的院子,乔氏心疼明暄,便把栖光院给了她,连明旭的院子都比明暄要小一些。
栖光院只明暄一个主子,下面几个丫鬟仆妇,自然明暄最大。
正屋是明暄的寝屋,同两侧耳房连通,左侧放置明暄当季衣物和饰品,右侧用作盥洗之地。东厢房辟开用作书房,明暄所有藏书古玩都放置在此处;西厢房除了客屋便是库房。东角与南春院打通,分了一小部分用作小厨房,偶尔熬药做些零嘴都在此处。
吴府只比栖光院稍大一些,却要住下八个主子,乔氏想想都替明暄憋屈。
此事明暄也不知该如何劝慰,沉默着不说话。
可是没过一会儿,便见乔氏打起精神,开始吩咐下人,“去牙行问问吴家四处有无什么空置的院子,有便去买下来!”
转头又对明暄说,“你不好同那武夫搬出去住,娘买处院子给你做库房放嫁妆总是可以的。你那些个书、衣裳、首饰,栖光院摆得满满当当,吴家哪里来的地方给你放?”
明暄有些哭笑不得。
其实那些东西也不是一定要带着的,只是看乔氏兴致冲冲不复悲伤,便也不阻拦她了。
***
三月二十七,诸事皆宜。
周氏带着钟秀花,并两个紫衣官媒,往宋家去提亲。
宋府正门朱漆厚重,宽八尺有余。广亮大门左右两侧,各有两座狻猊石像,四目正视门前访客,威武霸气,让人心生胆怯。
今日为交换细帖。
宋府开大门,洒扫门庭,一路丫鬟仆妇带领吴家一行人前行。转过角口,层台累榭,廊腰缦回。倏尔一座假山拦住去路,可是侧身回转,复是柳暗花明。又过一门,视野忽地开阔起来。一整片水池星星点点铺着青萍,成群锦鲤在水面下若隐若现。池边修了两道廊道,凌空在水面上,走在上面颇有几分趣味。
走出荷池,拐弯进入西府。
花厅内光线亮堂,两侧丫鬟林立,静默无声。
上首一位三十余岁的贵妇人,身穿一件银白琵琶烟罗衫,青莲烟云间白织锦襦裙勾勒出曼妙曲线,外披一件雪青掐花褙子。云鬓高髻,插梳一金镶蓝宝石掐丝镂花梳背。低头轻轻抿一口清茶,耳边的金花莲卉耳环便轻轻晃动起来。
举手投足间,皆是优雅。
周氏和钟秀花被乔氏这一作态唬得半天没说出话来,还是那媒人笑着把细帖放在桌上推了过去。
“唉哟宋太太,瞧您这一举一动,那可真是大户人家才有的仪态。素闻四娘子最懂礼节,有您这样的母亲,那可真是不见怪呢!今日呀,我们是想着为两个孩子交换细帖,您看?”
乔氏也不过分拿侨,让徐嬷嬷将准备好的庚帖与细帖递过去。
那细帖子要求写明家庭三代的姓氏、官职与田产。吴家递过来的不过薄薄一张纸,宋家递过去的可真就是厚厚一沓。
周氏和钟秀花心惊胆颤地接过那厚厚一沓细帖,翻都不敢翻开查看。前几日那张草帖拿回家,看着那一个个都不认识的字,一家人当真像踩在云端一样。越看越觉那宋家四娘当如九天神女,不是他们这些泥地里的人儿能触碰的。
来 APP 跟我互动,第一时间看更新